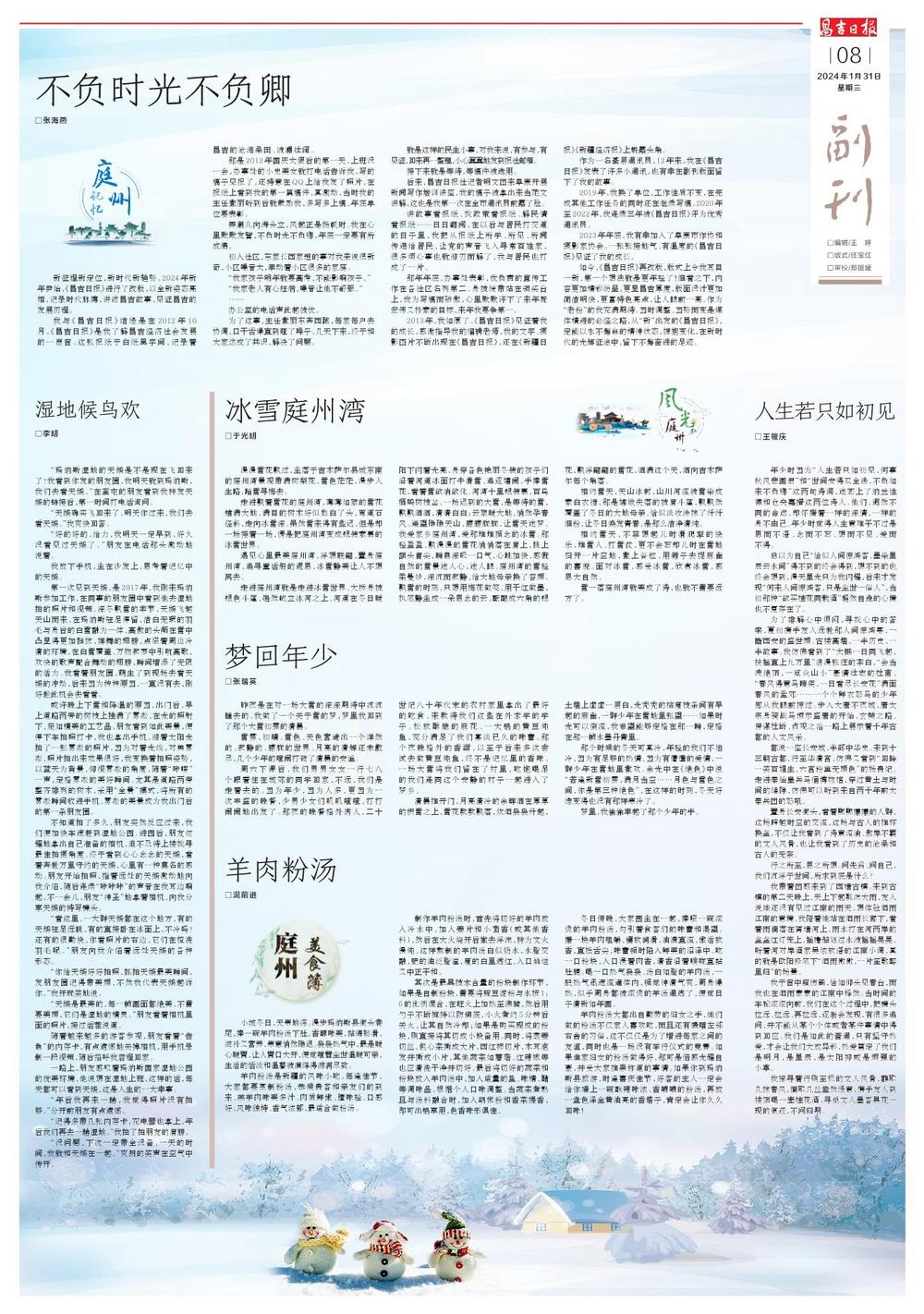□张瑞英
昨夜是在对一场大雪的深深期待中沉沉睡去的。我做了一个关于雪的梦,梦里我回到了那个大雪初霁的清晨。
雪霁,初晴。雪色、天色营造出一个浑然的、寂静的、朦胧的世界。月亮的清辉还未散尽,几个少年的喧闹打破了清晨的安谧。
周六下课后,我们男男女女一行七八个跟着住在城郊的同学回家,不远,我们是走着去的。因为年少,因为人多,更因为一次丰盛的晚餐,少男少女们叽叽喳喳,打打闹闹地出发了。那夜的晚餐格外诱人,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农村家里拿出了最好的吃食,来款待我们这些在外求学的学子。松软酥脆的麻花、一大锅的黄豆炖鱼,充分满足了我们寡淡已久的味蕾。那个夜晚格外的香甜,以至于后来多次尝试去做黄豆炖鱼,终不是记忆里的香味。一场大雪将我们留在了村里,吃饱喝足的我们连同这个安静的村子一起进入了梦乡。
清晨推开门,月亮清冷的余晖洒在厚厚的积雪之上,雪花款款飘落,炊烟袅袅升起,土墙上虚虚一层白,光秃秃的枯瘦枝条间有早起的麻雀,一群少年在雪地里张望……如果时光可以倒流,我希望能够定格在那一瞬,定格在那一帧水墨丹青里。
那个时候的冬天可真冷,年轻的我们不怕冷,因为有足够的热情,因为有懵懂的爱情,一群少年在雪地里撒欢。余光中在《绝色》中说“若逢新雪初霁,满月当空……月色与雪色之间,你是第三种绝色”,在这样的时刻,冬天好像变得也没有那样寒冷了。
梦里,我偷偷牵起了那个少年的手。